
“韭菜、好韭菜、“撇”高的好韭菜……”
巷道里来了个卖韭菜的小车,大家听到吆喝声,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赶将过来,瞬间就把卖韭菜的小车围了个水泄不通,这些人七手八脚拿的拿,称的称,一会儿就把满满的一车韭菜瓜分一空。这时候你再看,街道边、门楼边又到处都是三三两两边唠嗑边择韭菜的人。
距黄河不远的平陆常乐镇有个村叫撇“平”高村,那地方种的韭菜面积多质量好,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运送到附近的各市县供大家食用。
入了暑的韭菜刚有了苔,还不老,不过杆儿也还不是很长,而秋后剪去韭花的老韭菜虽长了根老苔,但白晃晃、脆生生的杆儿粗壮悠长的像根小葱,此时做腌韭菜最好。
在那上世纪六十年代,是在那物质生活相对贫瘠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,让人记忆深刻的少不了那一碟子曾养活了人的咸韭菜。
滴水成冰的十冬腊月天,简陋的小屋子里蒸汽迷蒙,几个小孩围坐在一张小桌四周,勤劳而又慈祥的母亲,给孩子们端上来几碗鸡蛋泡馍,桌子中间,俨然放着一碟子咸韭菜,在吃早点这场重戏中,咸韭菜是唯一的主角,这绝佳的套餐也深深的刻在了我的生命年轮上,以至于一直到现在也不时忆起,间或还要品尝一番。那吃的不是鸡蛋泡馍就咸韭菜,而是过去岁月的回放,是对母亲的感恩,是对童年的回忆。
那时,每到农忙时节,从地里干活回来,母亲去罐子里夹几筷子咸韭菜,放点红红的辣椒面泼点热油,就是一碟子好菜;冬天没有青菜时,每家每户的桌子上大多除了酸菜就是咸韭菜;中学生出去念书,装上一瓶子咸韭菜就是一星期的菜;我停学后在运城,每次去时装厂带上两瓶菜,也必有一瓶咸韭菜;后来,我在一家童装厂做缝纫活,那家的女主人腌了满满一小缸的咸韭菜,冬去春来,一天又一天,人多吃抢食,这缸咸韭菜,也被我们这十来个正当青春好年华的女子们吃了个精光。
不知从何时起,咸韭菜从主角的位置慢慢退居二线成了配角,又从配角位置淡出了人们的餐桌,现在的年轻人都去追寻味道浓重的各样美食去了,谁还记得起角落里还有一坛子咸韭菜。兜兜转转,尝遍山珍海味,鱿鱼海参,当人们舌尖的味蕾对一切美食都不再稀奇的时候,某一日猛的又想起了咸韭菜独有的风味,它不事张扬,静守孤独,只默默的呆在那里等你再回首。
好在韭菜是大众菜,随时都可以采买一把回来,择干净淘洗晾干,只取韭菜杆儿切成段,加盐拌匀,煮点花椒水晾凉,然后一并装入瓶子或坛子再加点米醋,放在阴凉的地方近一个月即可食用。
除了一般的简单吃法,你肯定没听过,咸韭菜还可以炒着吃,切点青辣椒和葱蒜,和咸韭菜一起大火翻炒,就着刚出笼的雪白热馍馍,也非常的好吃呢,不信你试试去!
青葱岁月去,沧桑人生久。不言巧妆扮,只将味道留。咸韭菜,有失落时也有得意时,这不,一不小心它登上了大雅之堂,成了某些饭店的招牌小菜,很受那些老板们领导们的青睐。大家闺秀有大家闺秀的风范,小家碧玉有小家碧玉的纯朴,咸韭菜,何尝不是用它那纯朴自然的一面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呢!
菜,还是那菜,时间不同,身份不同,却让人吃出了不一样的心情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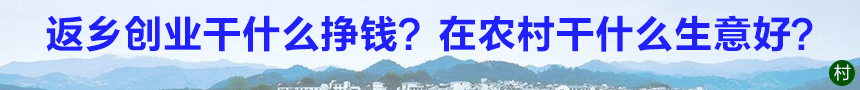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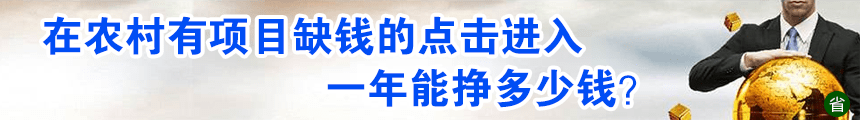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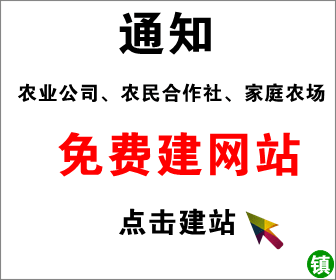
 苏ICP备18063654号-3
苏ICP备18063654号-3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
